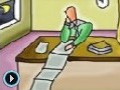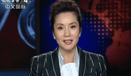在许多人看来,这意味着,一些政府部门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突击花钱时间。但财政部官方网站上、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的署名文章表示,虽然2012年年底财政支出规模较大,但并不是违反预算管理规定的年末突击花钱。
白景明的这一判断,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乃至质疑:年终突击花钱不违规?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哪些钱算违规?
突击花钱不只发生在中国
“年底突击花钱与违规花钱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白景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违规花钱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原本没有预算,但非要在一个项目上花钱。二是有预算但是不走正常审批程序。三是有预算也走程序,但是最后“做了手脚”。比如政府采购,有预算有程序,但最后没有把钱给中标的供应商。“这些情况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但是这不仅仅发生在年底,每个月都有可能发生。”
在白景明看来,突击花钱并不代表违规。这种预算支出的不均衡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日本2011年到2012年的预算年度最后一个月的支出,就占到了该预算年度总支出的14%。“有些预算本身就不是均衡支出的。因为有些项目并不是每个月都有。比如一些机构年底才会启动一些项目,如年底召开工作总结会议等等。因此不能用年底突击花钱等同于违规花钱。”白景明说。
白景明认为,公众对“年末突击花钱不违规”的指责主要出于两个方面:一是公众认为有些钱不该花。有些机构脱离预算,财政收入增加后,原本某个项目没有预算但是非要花钱,导致了浪费性支出。二是“原本有预算,虽然用不了这么多,但是年底非要花出去”。
为什么要突击花钱?
研究者认为,年终突击花钱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国现行的预算编制采用“基数加增长”的方式存在极大的缺陷。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因此各单位到年底必须把钱花出去,否则就要上缴国库,而且第二年的预算规模还会减少。
“有些项目如办公经费或采购经费,如果一个部门一年的预算是100万,年底完成这些工作只用了80万。上级就会认为明年80万也够了。这就会让第二年的预算减少。”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教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顾问施正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些部门可能会为了花钱而花钱,比如开一些没有必要的高规格会议或委派一些没有必要的出差学习等。”
此外,规模不断加大的财政超收收入也成为一些部门突击花钱的动因。
所谓财政超收收入,是指当年实际财政收入超出预算收入的部分。据全国人大财经委测算,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财政超收收入近5万亿元。
按规定财政超收收入除了按法律、法规和财政体制规定增加有关支出外,相当部分会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纳入第二年预算安排。然而,目前虽然一些城市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众多地方政府并不情愿将超收部分纳入监督,而是“开动脑筋,动员力量”将超收部分全部花掉。
日前,财政部财科所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年底财政支出规模较大,主要原因是:一些项目支出在前期准备阶段资金需求量小,后期实施阶段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大,相应资金支付也是前少后多;一些据实结算和以收定支的项目年底按实际工作量进行清算,12月份支出相对较多;预算安排的一些支出项目由于客观条件变化等原因,资金支付后延,其中有一部分资金还需要结转到下年使用等。
施正文表示,目前预算批复和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是脱节的。每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中央财政预算之前,项目支出中一般只有延续性项目按一定比例预拨部分资金,新增项目大都在预算批复下达后才开始支出,这就使一些资金只能延后支出。由于财政预算中只有总量(预算)的规定,并没有“花钱时间和进度”的约束,因此形成一年中财政拨款“前高后低”的尴尬。
而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暂无消息。研究者认为,在目前的现状之下,“年末突击花钱”和年底财政支出规模较大现象还将继续存在。
突击花钱花在哪儿了?
面对这种暂时无力改变的现状,众多纳税人更加担心自己所缴纳的税款是否已被各级部门单位违规花掉。
一位在地方事业单位工作的财务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很多财政拨款是固定的,比如人员工资费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一些专款专用的财政拨款则受到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等机构的监督,通常也不会出现大规模挪用或突击消费的情况。”
白景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12月份财政支出规模确实会大一些,但基本上都是经预算安排且根据政策和实际需要执行的支出,而且绝大部分资金是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
这个解释固然权威,但过于模糊。施正文表示,公众理应知道财政费用花在了什么地方,且这种关注不应仅仅聚焦在“年底突击花钱”上。正是因为一些部门单位大笔花钱“不透明”,才让年底时段的开支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纳税人应当有权利得知公共财政的使用情况,“但这些信息并没有得到公开。如果公民想知道年底大量的支出可以去政府主管部门申请政务信息公开以满足知情权。”他认为,让财政支出更加透明可以让公众更加了解“年底突击花钱”的真实情况。
评论
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1.9%,这是今年单月财政收入增速首次高过20%。但1—11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9%,增幅同比回落14.9个百分点。年初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安排的全国财政预算支出为124300亿元,而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支出为104896亿元,全国财政部门或将在12月完成突击花掉约2万亿元财政预算支出的任务。
政府年底突击花钱,已经成了周期性问题,每到年底舆论都会警觉起来,提前为突击花钱打预防针,财政部也多次表态严厉禁止,但这个痼疾很难根除。今年以来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通过各种非税收入,地方政府仍能实现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而且前一阶段增速减缓而压缩开支的压力,将在这一阶段集中释放,年底政府突击花钱的冲动将十分巨大。
遏制突击花钱,靠年复一年地表态,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突击花钱源头在预算编制问题。按照现行的基数预算模式,本年度的预算是以上年度决算为基数,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定数额,结余全部上缴。这样一来,上一年的实际花钱数额,反而成了下一年申请预算的参照,上年度结余多少,下年度预算就扣减多少,节约了反而吃亏,为了保证来年的预算,当然会在年终大撒把,把这个编制预算的基数给抬上去。
以此来看,预算编制改革是必然,要通过预算编制改革,形成奖励节约惩罚浪费的财政支出奖惩原则。从认识层面讲,这一原则不具有什么争议,每年年底各方也都是这么呼吁,但预算编制改革依赖于《预算法》,而《预算法》自2005年开始修正,就一再搁置,何时修订出台至今未明,《预算法》出不来,改预算编制也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预算法》修订的搁浅,本身反映出预算编制体系转型之难,地方政府已锁定了现行预算资金的分配机制,这是个自然而然的惯性轨道,而且中央和地方有着各自的财权、事权,地方不可能从宏观层面去理解整个预算编制,想要让地方形成节约意识,在预算编制改革进展难期的前提下,只能对政府花钱建立强有效的监督机制,对预算编制从严审批,对预算项目深入细化,对预算支出建立动态监管以及绩效考核机制,间接地树立起花钱有道的刚性。
需要明确,批判突击花钱的前提,是担心突击乱花钱,如果钱花在了民生短板上,所谓突击花钱就是个伪问题。目前的预算编制,很大程度上是相当模糊的,门类没有细分,预算内容通常是几个大的支出项目,政府因此具备了在年底突击花钱的弹性;与此同时,各级人大对预算编制的监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预算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体清晰,缺乏权威的干预和认定;此外,政府预算支出有没有花到点子上,花得有无效率,也没有绩效考评机制,对预算通过之后政府后续花钱缺乏动态的监管,给其不顾效率突击花钱制造了机会。
部分项目从预算申报到资金到位要走流程,这些积压到年底的支出没什么问题;一些年底突击花钱的项目,确实把钱花在了该花的地方,这些支出也没什么问题,问题的关键是,那些类似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式的低效益乃至负效益支出,才是年底突击花钱的病灶,而这些病灶的根源,还是权力问题,权力弹性过大,权力不够透明,权力运行没有纳入程序轨道。